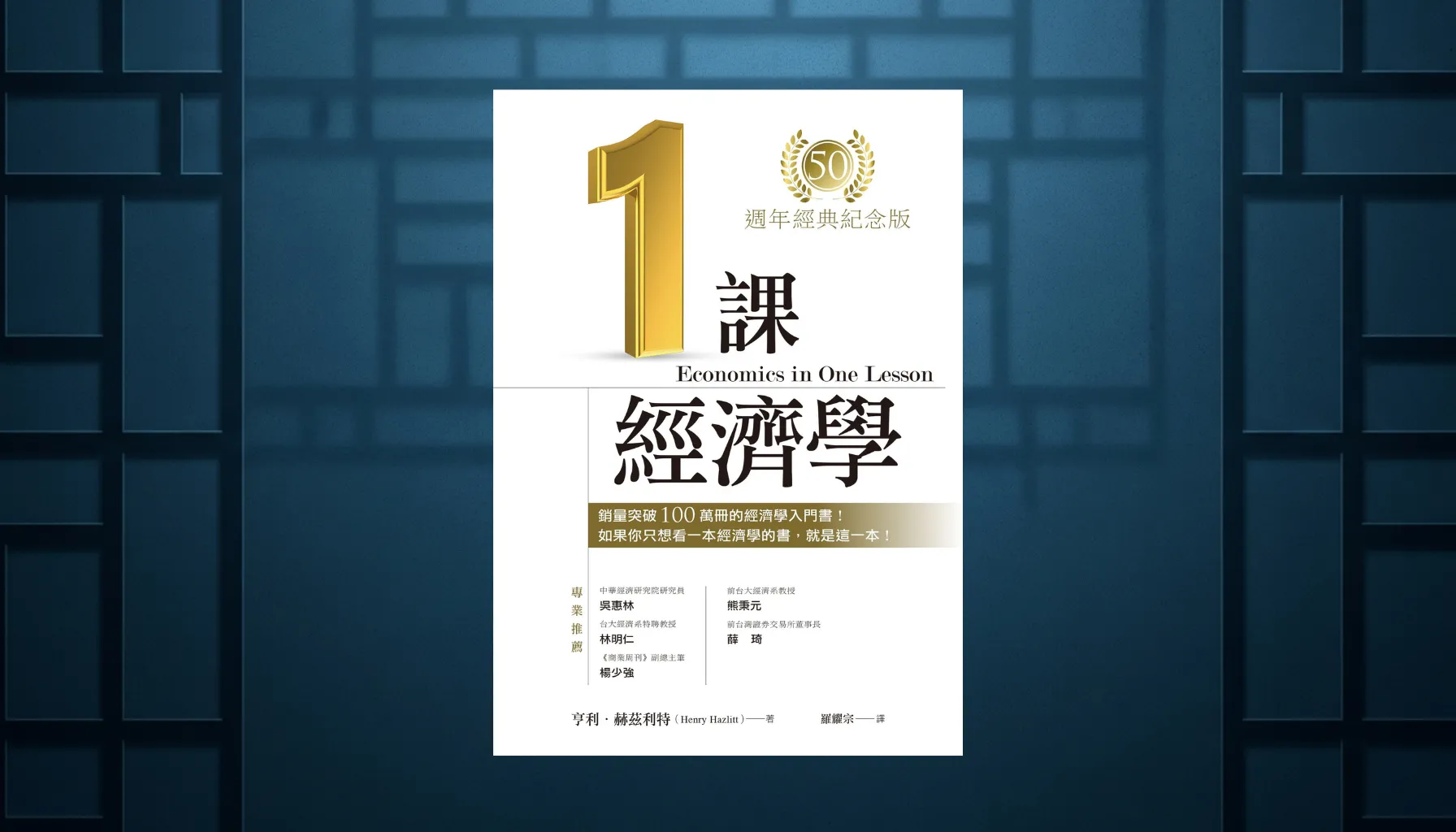
《一課經濟學》:一堂課看破短視迷思,練就長期大格局
2025 Jul 10 經濟學
前言
從開始閱讀《一課經濟學》這本書之初,我便非常驚訝於它悠久的歷史,本書第一次出版的時間為1946年,距今近80年,那年的台灣才剛從日治時期轉換為國民政府時期。從初版發行後不斷再版,且全球總銷量已經超過100萬本,由此可見這本書的歷史地位有多麼崇高。
本書的作者——亨利.赫茲利特(Henry Hazlitt),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與記者,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專欄作家之一,他畢生致力於捍衛經濟自由,對政府干預經濟政策提出諸多批評,強調經濟政策應考慮長遠與全面的影響。
在本書中,他用淺顯易懂的方式,從社會上的各種案例說明了許多經濟的謬誤,包含了破窗戶、行業擴張、政府介入市場……等等。
他在書籍的第一堂課就寫了一句話定義經濟學:
經濟學的藝術,在於不只觀察任何行動或政策的立即影響,更要看較長遠的影響;不只追蹤政策對某個群體產生的影響,更要看對所有群體造成的影響。
在接下來的整本書也不斷強調同樣的概念。這也就是我認為貫穿整本書籍的核心思想——「破窗謬誤」以及「長期觀點」。
破窗謬誤
本書的第二章便提到了這個遍佈在各個章節的重要概念。
破窗謬誤是法國經濟學家巴士夏(Frédéric Bastiat)在1850年(是的,也是非常久以前)提出的。內容的大意是:一個小孩打破了一家店的窗戶,店主必須花錢修窗戶。旁觀者說:「這樣也好,修窗的師傅有生意做,這樣能促進經濟活動。」
我們從小或多或少都聽過爸媽跟我們講過類似的言論,看似有道理對吧?但這就是個謬誤。
謬誤的地方在於,每個人只看到修窗的師傅受益(看得見),卻沒看到店主原本可以把這筆錢拿去買鞋子、投資或儲蓄(看不見)。大家認為破掉的窗戶將可以促進「修理窗戶」這個經濟活動,但其實玻璃店新接的生意,可能只是從裁縫師傅損失的生意那邊得來的。整個過程,並沒有增加新的「就業機會」。
破窗謬誤的概念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發:「看問題時,是看整體,不是看片段」。
關於破窗理論,在書中說道:
所謂深入了解經濟學,是指探討一項政策產生的所有影響,不是只看眼前看得到的事情。
這句話將破窗謬誤的概念延伸到了政策的制定,這也是支持自由市場機制的重要理由。
書中舉例,政府常會為了「救某個產業」出手,像是補貼農業、幫汽車業振興。出發點是好的,但問題是,當政府把資源撒在一個產業身上,就代表其他地方拿不到這些資源。這就像破窗的故事,玻璃業者賺到錢,但那筆錢原本可能是要去做一套西裝的。
更不用提的是,政府出手幫忙的方向也不一定正確,有時還補貼到一些早該退場的夕陽產業。你不會為了光碟機廠商的飯碗,就去限制音樂串流的發展吧?讓市場自己決定誰該留下、誰該退出,才是真正有效率的做法。
總而言之,破窗謬誤就是在提醒我們,看事情千萬別只看片面而已。
長期觀點
經濟學中有很多不同觀點的學派,而「長期觀點」(long-run perspective)是古典經濟學派的重要立場。古典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首推提出「看不見的手」想法的經濟學大師亞當.斯密(Adam Smith)。
這個學派也非常強調自由市場具備自我調整能力的機制,只要讓市場自由運作,雖然短期可能會經歷失業、產能閒置,但長期來看,經濟會自然恢復活力。長期是重點,市場需要足夠的時間來找到新的平衡點。
這立場與凱因斯學派的短期主義形成強烈對比。凱因斯曾說:「長期來說,我們都死了。」他的意思是:如果經濟當下在衰退,就不應該長期等待市場自然修復,而該透過政府支出、刺激需求來救市。但這種做法對古典學派而言,是本末倒置的短視行為。
凱因斯主義的問題在於,他們忽略了政府干預的長期後遺症。
書中以政府出於「保護農民」的立場實施限產政策為例。看似是為了解決價格下跌與收入不足的短期問題,實際上卻忽略了市場自然調節的長期效果。
在自由市場中,會被淘汰的是高成本、低效率的生產者,資源會逐步集中到更有效率的農民與土地上。這樣不但不會減少總產量,甚至還可能以更低的價格生產,讓消費者花少點錢獲得更多購買力,進而帶動其他產業的消費與就業,提升整體經濟效率。
相反地,當政府一視同仁地限制所有農民的產量,反而讓原本應該退場的低效率生產者繼續占用土地與資本,造成資源浪費,也拉高了整體平均生產成本。相較之下,消費者將因此花更多錢買更少的東西,購買力減少了,經濟活力也被壓抑了。這種政府的干預雖然短期內穩住了部分人的收入,長期卻可能阻礙了效率提升與產業轉型。這其實就是用全民的納稅錢去撐住本該自然淘汰的低效率者,結果導致是整體社會付出更多、得到更少。
公共建設也是一個常見的例子。當政府缺乏長期思維,為了應付短期高失業率便推出公共建設計畫,卻沒有先問清楚:這些建設本身有沒有長期價值?是不是人民真正需要的東西?
結果往往是建設完成後,很快就淪為閒置資產。錢花下去了,場館蓋好了,但沒人用,最終只留下得繼續維護的「蚊子館」。而當初舉債蓋出來的建設,終究還是得有人還帳,不是未來稅賦增加,就是靠印鈔票製造通膨,由全民買單,甚至把成本一路轉嫁到下一代身上。
像《小島經濟學》書中也提到一個極端例子──政府竟然在沒人要去的沼澤地蓋燈塔,只是為了提供工作。話說回來,其實這也是另一種破窗謬誤,看到了工人有工做、水泥有倒下去,卻沒看到那些資金原本能在其他地方創造更多真正有意義的產值。長期觀點與破窗謬誤息息相關,都是讓我們更有大局觀的重要概念。
我的觀點
破窗謬誤
如果要將破窗謬誤應用在經濟學以外的地方,我第一個想到的會是決策。
毛治國教授在《管理》一書提出了「見、識、謀、斷」四部曲(延伸閱讀:《管理》:讓毛治國的四段論模型為你的決策打底),其中在「謀」的階段裡介紹了「推後果」的環節,這個部分便跟破窗謬誤有異曲同工之妙。當我們在做選擇、決策時,能推測出做決定後的後果並事先設想配套措施,是個很重要的超能力。畢竟所有的事情變不會總是如果們預期般發展,有太多的意外會隨時發生。多想到一個不同的後果,就多一份安心,預先想到的周延計劃能幫助我們應對意外,就像是一張網子,能接住我們,不至於掉入無法挽回的深淵。當然,這個網子不會無限延伸,終究會有漏網盡頭,但只要我們持續觀察、練習,這個不看片面、推測後果的大局觀能力就會像是去健身房練肌肉一樣,越長越強壯。
長期思維效應:經濟學也能拯救世界
前台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薛琦,在推薦序講的非常深入我心。關於凱因斯學派的名言:「在長期,我們都死了」,薛琦為這句話再加了下一句:不要忘了,「我們的子孫還要活下去」。
是啊!例如公共建設,我們不能只是為了短期為了創造工作機會,不顧該建設的實用性就舉債開工,或許幾年內的失業率會下降,但倒霉的是我們下一代,他們完全享受不到這些建設,卻需要為這些設施買單,這很明顯對他們並不公平。
相同的概念可以完美轉換到環境保育。最近一直很想看紀錄片導演——舒夢蘭所執導的《守護我們的星球》。
這是台灣首部橫跨南北極、歷時15年所拍攝的生態紀錄片,片中記錄了冰川的崩裂、物種消失的危機以及生態失衡的劇變。我們是地球幾十億年以來第一個能改變環境的物種,工業革命、飲食習慣深深地影響了整個世界的平衡。人類對環境的劇烈破壞從南北極開始發酵,隨著地球持續受創,長期下來,我們的日常生活勢必迎來巨變,從近年屢破新高的溫度,以及極端天氣頻率增加的現象,都已初露端倪。
所有的長期效應都從微小的改變開始累積,幾家排放黑煙的工廠營運幾年,不至於讓北極熊瞬間沒了棲息地;砍掉幾塊熱帶雨林,不會立刻讓全球升溫失控;丟進海裡的幾條一次性塑膠袋,當下也還不會立刻把海龜的胃堵死。但就是這些不痛不癢的小破壞,年年疊加,最後把地球一步步推向臨界點。
相反地,我們也能從微小的改變開始做起——今天出門就自備環保袋,盡量不用一次性塑膠袋(很方便我知道);午餐多點蔬食(也有很多好吃的選擇),少吃紅肉;隨身帶環保杯(不要為了造型買很多個),拒絕塑膠吸管。這些看似不起眼的選擇,日復一日地累積,也能讓地球慢慢喘口氣。
我們的每個舉動都像是投下一張選票,你要投票給繼續破壞環境,還是保育環境、留一個美麗的地球給下一代?
最後,我想為凱因斯學派與薛琦的註解,再加上一句異想天開的話:「在長期,我們都死了,但我們的子孫還要活下去;說不定下一輪輪迴,你還得親自回來收拾這一切」。






